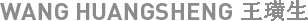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大概是在 “游·象”系列时,王璜生从对“游”字的心有戚戚,开始明确自觉、舒适地去应对现时的物象和思虑。与 一团乱电线的“境心相遇”,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开始,一团没有头绪的乱线,既是他面前的物象,又是他必定所处的当代位置,只是手下的笔,数十年的研习塑造出的感性方式该如何回应这种时刻。这岂止是一人一事的境遇,共临其境,却只能各自修为。
那一物象对应了他积蓄已久、理不清的很多纠结,他说,“比如中国水墨与今天现实的关系,与我们面对的艺术的多种形态的关系,与当代艺术方式的关系,存在着多重关系,如何去梳理”?
相关的问题已经有百年的讨论,都把对水墨或中国画的继续置于一个新的的历史境遇中,曾经是个古今问题,或作为一个资源性因素的观念、技法问题,或作为文化身份的他我问题,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真正的纠结所在是,这些都不再是他我之间的权衡、吸取、体用的问题,而成了“我”的内部表征,“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他者的艺术,反之,他者的艺术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内在部分,参与我们的感知和判断。所以,我理解王璜生经常说到的所谓接轨、所谓国际间的对话,一方面是他作为馆长日常料理的视野和策略,另一方面的急迫感和纠结感可能来自这种内在的需求,来自寻求内在的完整感和自主感的需求。在古典文化中当“境心相遇”时,“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匠心,得物而后开”,如今,我们内在地拥有不同质地的文化,心本身是个万花筒,得物之时,不再是匠心开物之事,更是重建视觉方式之时。这岂止是艺术家的问题,干脆就是我们每天的必遭之劫。艺术家把这种努力外化为作品时,就不再是私人的功课,而是一场战斗,在一个现实的视觉语境中,去实践它。
王璜生第一次画这种缠绕线条的时候,很多朋友自然会想到,是因为美术馆的工作太烦杂,头绪多,理不清,所以画随心象。而王璜生并不以为是,他自认为还是“对文化问题的追问,对主体出发点的认识,人总有自己的出发点、情感的立场,思想的立场”,这使他愿意尝试着干脆就呈现这种纠结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文化态度。
因此,这些问题也不再是如何融汇不同资源的知识化问题,而是如何在自己的精神上形成完整表达的努力。这是批判性的否定或终结论的预言都无法化解的,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王璜生所说的纠结:在绘画中,他摆脱不了水墨历史中发展出的种种精微趣味,那个强大的系统不仅给研习者赋予一种感性方式,也塑造表达方式。他曾尝试过摆脱,但总有更感性化一部分很难去忘掉,因为这不只是你所拥有的历史,而且是你之所以是你的构成部分。他说:“这种东西会形成一种判断,一出手就是这样,而不是出于刻意的坚持”。而且这种判断有它稳定的图式表达,它来自于与自然物象的“境心相遇”,但在如今的生活规则和逻辑中,物已不似,心亦非也。
所以王璜生一直在想象“如果能斩断表达的惯性,会怎样”?我想,他首先疑虑的是真诚的质地。如果不斩断惯性,那是对身处其中的生活和世界的无视。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无视,坚守古典的方式,像辜鸿铭。这非常容易走向一种原教旨价值观,形成一种对抗性的忠诚和英勇,这种坚持作为我们思考变化的一种参照,自有其文化价值。如果彻底斩断惯性,那就是对自己的恩断义绝,从何处出发将会成为新的困境,且不说这是否可能。
在研习水墨画之中,王璜生体会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世界观,从“易”中化生出“游”的感性能力。至于线的具体使用,这种笔下功夫的修炼和运用,在他的藤蔓、残荷等作品中已经能看到他与那些图式的对话和较量,直到那团乱电线的出现,并且“如实”地表现它的时候,他从中发现了一种既不因循、同时也不负他水墨感受的视觉方案。于是,在线的游弋中,游,也从一种美学惯性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而在其中获得的自在的体验对王璜生可能至关重要。如果按照德勒兹的解释,体验状态在本质上可能不是主观的,而且它不是个人的。它是绵绵不断的流动,是混乱的流动。它潜藏于所有符码之下,是对所有符码的逃避。
这让他能够有意识地与既成的图式拉开距离,即使是他自己的所游之象。有一次我在他的画室聊天,他说到,“回头看‘居间’中的一些画,自己和一些朋友都会觉得非常好,但是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方法。就是因为太像传统画了。还是没有游出来”。所以,那些游动的线既像游牧的线,也是逃逸的线。
同时他意识到“提纯”这个观念很有效,他说:“当我们谈到传统绘画时,什么厚重啊,滋润啊,都来了。这些说法太容易陷入具体的文化情感,甚至是特定的文化感受。还有一个问题,用古代的语法能否说清楚当代的感受和事情?那我就想我是否可以提纯一点,在传统绘画中,那些非常丰富、非常有表现力、讲究特别多的东西里面,如何提纯,包括提纯成一个线条,在一个线条中也可以去深入地理解和感喟的一些东西”。
提纯是他与传统的习惯性感受拉开距离的有效方法,终究不只是为了创新一个视觉图式,而是要来回应我们身处其中的美学环境,回应与多种艺术语法的相逢相遇,回应他自己的纠结体验。
王璜生说“在我们用笔墨修养说古代的生活时,可以和今天非同好者没关系。而当代艺术就是要强调对当下问题的介入,有针对性的批判、调侃和解构。但中国的水墨精神强调一种更为诗意的思考,更为超脱的表达,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处理?现实的文化空间发生的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实地面对一个更国际化的语境中,更开阔的文化空间,这首先是个前提,而基础是他的水墨修为。对于王璜生,放弃水墨研习中的文化体会是不真实的,而无视眼前的文化空间可能把艺术变成私人之间或同好之间的游戏。如他所说:“我对传统的这种水墨特殊的审美,特殊的这种文化内涵的关注是会比较多的,也努力想去呈现它,好像说我现在用的很多线条自由的游动等等,这里面可能也跟中国绘画比较讲究线、笔墨有关系,也跟中国水墨讲究一种一种游,很自由、很游动、很自在的这种文化追求有关,当然我又站在一个当代的角度上,也希望说我们的绘画,我的绘画能够摆脱传统的某种陈陈相因的一种视觉的表达方式,而进入一个当代视觉的一种氛围环境里面”
他喜欢说修为和自在,“这好像是一对矛盾。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矛盾,或生活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展开的”。他说的修为,不仅是在心理的、人际的、杂务的等各种限制下的安然自处,还有与不同的文化资源和复杂现实共处的自在。
当他把“游”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后,游才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手里的线条不必拘泥于再现或表现,它也不必纠缠水墨新与旧的问题,只有好的水墨在坚硬的现实、锋利的物象、矛盾的处境面前,如何游动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线条好似随意,但它不同于无意识绘画,无意识绘画更强调绘画时的即兴能力,或即兴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规则或技术化要求刻意的破坏性,以通过无意识来唤醒某种被规则限制了的、或压抑了的本性,故意降低技术性,要保留下那些即时的感想。但在王璜生熟练的水墨绘画中,情感的表达是经过训练的。无论线条或笔墨,不只是形式,或熟练的技术,而是一种研习的结果。其中虽然有技术性的精进过程,更包括在这个过程中的性情修养,这是一个有意识无意识过程。所以他说:“不论是在看展览或在自己的绘画中,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在这个过程中的修为的运用其中,也运用到一个简单的线条上。它的讲究包含在各种方面,包括审美,包括技术,甚至包括指尖与纸的接触。具体到一根线条最终走向哪儿,怎样走,好像没有很确定的预设,这时手将怎样走笔,好像不那么确定,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转,好像是线和笔也参与意见,如果能转就转,如果不适合转你硬转,结果就不对了。这其中有很多属于很微妙的东西,这种东西反应在线条上,就可能带出很综合的情感的变化,以及线条上变化”。
在这里,线条的趣味性成为一种新的自觉。看到2008年他的一张“无题”时,我还有一种臆想的后续动作,就是在那些线上面添加上一些黄色的彩点,似乎就可以变成完整的一张藤蔓、残荷的画。现在这条线的游象幻化出的不仅是越来越丰富的画面,也可幻化出锋利、危险的铁丝网的意象,这个意象似乎呼应了最初的电线给他的暗示,重新赋予游象一个清晰的性质,一种比较纯粹的视觉图式,也给他的古典意趣的水墨笔法赋予了现实的情绪和使用途径。
现成品铁丝网被引入时,他在保留其现成品形态的同时,利用幕帷和灯光的效果,建立起水墨的线与现实成品的关联,虚实之间,截然异趣。盛夏之时,我在王璜生的工作室又看到了这个铁丝网,它不再有虚影对映,而是被盘结成一个沙发,透明的材料封在表面。当他使用玻璃来结构游走的线时,材料的可塑性和易碎性质,以及铁丝网直接的刚硬暴力,与水墨的线在视觉上的相关性,就不再是制造幻影的戏墨。在这里,水墨既是王璜生解码的对象,也是他解码的手段,但可能因为他视其为“游”之所至,所以无论材料怎样变化都既不会带来对水墨认同的破坏,也达成了他不愿被编码的努力,让艺术能够持续保持着与自己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