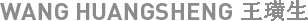文/王璜生(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的当代艺术包括当代摄影,其创作的思想资源及图像生成内在动因,有不少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中国的文化、所处地域的传统与现实等等,这样的思想资源及图像生成机制,其构成的原因及内在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有如对红色历史、“文革”历史及其视觉图像等,艺术家是如何以个人的立场及表现的方式,针对、延伸、挪用、反思、反讽等,对这样的历史进行思考、表达和回应。而当我们无法触碰历史的本身时,图像成为我们解读及反思历史的利器。
那么,所谓“红色图像”其所指和能指是极具丰富的复杂性及开放性的。一般来说,谈到“红色图像”,我们很快就会联系到“文革”,因为可以说,“文革”是红色图像登峰造极的表现,“文革”以一种癫狂的精神状态和激荡的社会症候,呼应着世界的红色狂热的风潮,其图像的形成、推动及传播也达到了疯狂和巅峰状态。然而,我们对“文革”是多重敏感的,既有政治的,讳莫如深的、痛苦的、禁忌的、理想激情的、峥嵘岁月的,也有家族家庭的、个人的、知识分子理性思考的等等,这里面有太多复杂的记忆和情感,包括有太多的伤害及关于伤痛的记忆,也有很多想逃避但无法逃避的罪、恨、悔!当这样的“文革”图像成为了“红色图像”的巅峰代表时,我们的论述就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充满痛苦的反思的。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红色图像”,并不能等同于“文革”图像,“红色图像”的生成其实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甚至更早,这种图像的生成原因及过程是非常庞杂的,包括政治、时代、文化、阶级、革命、国际等,同时也包括民间、大众化、习俗等等,中国民间的明亮而直接易懂的图像特点,往往是“红色图像”最容易也最可直接利用的资源。“红色图像”最主要的社会学和美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具有浓郁的政治及与政治相关的时代形象和样式的;表现为通俗化、大众化的;有利于宣传传播的;明亮、正面、漫画式、直白性的等等。
而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及摄影与“红色图像”之间关系的解读,并不仅仅停留在视觉生成的关联性或情感观念的延伸关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其相关的针对性和借用、反思的空间,并将“红色图像”作为“历史”及历史的解读对象来进行新的思考、感悟和表达。
因此,在解读“红色图像”与中国当代艺术包括当代摄影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红色图像”往往被指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决定性瞬间”,它本真的记录构成了历史,而当代艺术家却针对了这样的“历史”图像进行重新解读。作为解放区最重要的摄影记者沙飞、和作为大型彩色画报社记者的翁乃强,他们以一种本真的态度,记录下种种的“历史”时刻,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及政治的背景,也包括特殊工作身份和情感因素,以及他们对瞬间的艺术敏感及镜头的把握能力,在他们的工作及镜头中,“瞬间”被定格为“历史”,“历史”被永恒的图像化视觉化;而成长于“文革”之后的张大力、莫毅、王庆松、蔡东东等,却以独特而超凡的解读“历史”的敏感及再造“历史”的能力,企图深入到“历史”和人心的深处,再造“第二历史”或“第二现场”。张大力《第二历史》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种介乎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劳动。作为艺术家,他具备了艺术的敏感和直觉及对图像和视觉的创造性解读能力,在貌似习以为常的社会图像中,他富于敏感性和创造性地构造了对问题的追询和图像的揭示,使我们“有趣”地进入一种艺术解读“历史”的情境。而作为准社会学者,他的尖锐、执着和严谨,体现了对历史和社会的理性追问精神,他的图像及档案的普查性工作,为我们积累了许多思考和叩问人性和历史的资料基础。那么,蔡东东的系列作品包括摄影装置等,有一种回到历史现场,或窥视历史的奥秘,而且幽默一番的感受。这样的幽默感更可能是一代人对另一代入的一种认知和解读。而他近期一直在收集的图像并创造出的新作品,是巨量的那个年代的个人照和证件照片,照片背后还有一些留下了文字记录:时间、地点、友情等等及证件用章等,这些所蕴含的时代的信息量,及图像本身静默的力量,是对一种历史严肃而深情的回应。莫毅则带着一双“红色”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在他的镜头里,一块普普通通的红色床单,会被误读为一面旗帜;一堵斑斑驳驳的红墙,人处于其间,仿佛进入了红色的历史年代,连表情都进入了状态。王庆松是一个独特的另类,往往将自己扮演为历史的在场者,而这样的“历史在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转换为另样的“历史现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转换为无处不在的“广告”,而人在其间变得如此渺小而无助。
我们经常会被历史的瞬间所迷惑,其实,我们很难弄清楚究竟“第一历史”是历史的“真实”,或“第二历史”更具真实性? 我们也许是在以艺术的方式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现场。
二,“红色图像”也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方式,一种集体主义的情结与表征,往往,镜头所“对准”的历史现场,或历史方式,其本身就代表着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象征,如“大礼堂”、“大宣传栏”、“集体合影”等等。当然,当代艺术家的镜头与思想、情绪的维度是与反思和审视历史相关联的。慕辰和邵译农的系列作品《大礼堂》,中国式的礼堂是集体化时代的产物,曾经是“净化和改造”灵魂的场所,是中国人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汇聚地,当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的思想、精神、政治理想、生活越来越多样化同时也物质化的年代,礼堂也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迹”。慕辰和邵译农持续多年,走访了延安、瑞金等革命圣地,也深入于中国的乡村与工厂,希望在这样的“大礼堂”中重新解读历史的现场,追问历史与现实中精神、理想、情怀等的种种焦虑与问题。何崇岳曾经以他的《计划生育》系列作品深有影响,那种同样深入人心和充斥视觉的“大宣传栏”,无疑是“红色图像”最有效的传播推广方式,而这样的宣传栏所传播的政治理想及政策导向,引导着主导着甚至“规定”着几代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的方式,今天,“计划生育”已成为了历史的“遗迹”,而“后遗症”则变得无法言说的复杂。何崇岳由此延伸的作品《终点》,关注的正是中国乡村遗存的现实问题。他所采用的“集体合影”手法,也有意味地借喻着“集体主义”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述。另一位借用“集体合影”方式,将行为、组织、表现、隐喻集合为一体的是当代艺术家庄辉,他从1996年开始,创作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群众大合影作品,他每次组织多达几百人的工人、农民、医生护士、解放军战士、学生等,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旋转式全景相机,进行集体大合影,而艺术家本人的形象总会出现在每幅画面的最右端。
集体的、权力的空间往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甚至,这样的空间更有着其神圣性和神秘性,这正如我们无法靠近“集权”中心空间一样。然而,渠岩却对这种“权力空间”的民间存在进行挖掘及记录,生动的记录了这种穿越时间与空间而一直延续存在着的特殊象征,丰富有趣的细节为这样的“权力空间”增添了时代的印记。
三,“红色图像”不仅仅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仅仅是一种集体表达和集体的记忆,而当时间和现实情境的推移变化,它们往往更成为了生活成长于其中的个体的种种个人记忆和情感轨迹,这样的记忆和轨迹构成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巨大空间,尤其是当个人、时代,与历史、集体相遭遇时,这种叙事方式及结构就有着深长曲折的意味了。曹凯的《六九年夏天》将个人的成长经历放在巨大的中国革命与世界狂热的背景下,世界到处的躁动、动荡、疯狂、激情、不安等等,欢呼声、摇滚乐、横飞的热泪、坦克的履带声、丛林的爆炸热浪、振奋人心的演讲等等,成为了像曹凯一样的这代人婴儿时期的“摇篮曲”。而王宁德宁愿永远梦游于自己的童年岁月和情境之中,军人的梦、红领巾的梦、家庭的梦等等,不知道是一种对安宁的渴求还是孤寂冷漠的心态,在这代人的内心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轰轰烈烈背后挥之不去的逃离感和拒绝感。宋永平将自己与父母辈的关系,和对父母的重新感知的过程及方式,以一种沉重的表现方式直逼心灵地呈现于视觉,使我们不忍卒“睹”的面对“父母辈”的身世与身体。而冯梦波这位“游戏电脑大王”,用互动的、参与性的及近乎游戏的方式来呈现和解读“私人照相簿”,私人的历史与公共的历史叠合,游戏式进入这样叠合着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新的进入方式。同样是“照相簿”,海波的图像却是凝重甚至沉重的,岁月、友情、事件、家庭,图像的呈现,艺术家既像是旁观者,又好像是亲历者。历史、时间、个人与社会,都很难以线状的方式来解读。
四,对历史本身的拷问,或对历史的问题延续性追问、调侃、挖掘及消解,试图表达对时间、生命、历史、记忆等的质疑。王友身的《冲洗》系列,从早期的对“大同万人坑”历史记忆的反思,到近年来公众参与性的冲洗—--记忆的逐渐消失与虚无,追问于人性健忘的特性。而这样的“冲洗”,是人性的有意为之,有意尽快地抹去不断褪色的历史,还是这褪色甚至消亡着的图像更隐喻着历史的“真实”和“永恒”?而何崇岳用静默而精细的镜头,将历史的带着“革命”想象的痕迹富于质感地记录下来,而这样的历史和革命的痕迹,无声地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而在历史的流变中,却变成了熟视无睹的现实残存。邵译农、慕辰曾经拍摄的《红卫兵墓地》,阴郁、潮湿、发霉、冷漠的现实,与曾经的理想、激情、冲动、狂热形成了太过于无情的对比,历史与现实总是如此的冷暖无常和无情。
深有意味的是,张克纯的《举着毛泽东像游黄河的人》等作品,曾经的历史,曾经的深入人心的毛畅游长江的事件和图像,在时间的变迁及地点的转移、思想的变革和社会的翻天覆地之后,依然呈现着一派历史的情怀和景象。而恰恰,在张克纯一系列的镜头里,历史的遗迹与当下的方式总是那么安静祥和地共处,却总是感觉到好像哪里“出错”了。这样的一种错位感正是我们对中国当代摄影与“文革”、与红色图像之间关系的最有趣的注解。
2017/5/28完稿于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