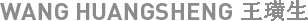库艺术=KU:从“游·象”系列,到“线象”系列、“箴象”系列,再到装置、影像,您的艺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为什么会在几年之内出现如此多的变化?在这种快速变化中怎样将每个系列作品所探讨的问题阐释清晰?
王璜生=W:其实应该说是丰富,我的作品和整个创作思路有一个自己的线索,从“游·象”到“线象”之间是一种衔接关系。“游·象”系列画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用铁丝网,开始做装置,其实做装置也是在考虑铁丝网和水墨之间的关系,诗意与危险性带给人的感觉,关于人性与社会性问题的探讨。
从水墨线条转向装置的第一件作品是《隔空》,《隔空》是想利用铁丝网的影子探讨其与水墨的、诗意的线状表达之间的关系,表现诗意与暴力之间的转换与对抗。到了《溢光》开始探讨玻璃与铁丝网之间的共构与冲突,后来又引入了纱布,这些作品开始出现伤害的主题,伤害与纱布的疗伤作用是相连接的,既有疗伤的一面,也有被伤害的一面。纱布包扎是想裹住残暴与危险,但同时纱布自身又受到伤害。这个理念在这次展览中转换为“缠”系列的第二个作品,将缠绕纱布的铁丝网置于鼓风机上,使纱布被吹起来飘起来,这时铁丝网和纱布之间的纠缠会产生挣扎的感觉,一方面鼓风机的声音非常有震撼力,而飘散的纱布既美丽,又是一种挣扎的状态。其实在用纱布做装置之后,我也开始用纱布做平面作品,包括这次展出的“痕?象”系列、“箴象”系列、“墙”系列等,都是用纱布进行平面创作的结果。
KU:铁丝网,绷带,鲜红的十字架,呈现出一种焦灼,恐惧和危机感,没有了早期水墨作品中的流动感和诗意,这种转变是来源于某些事件的刺激,还是源于您对当下性,社会性的持久关注?
W:应该说是个人关注视角和创作思路的持续性发展吧,其实早期创作“游·象”系列线条的过程中,我想探讨的问题在于水墨的经典性与当代性之间的关系。经典的水墨是对线条的提纯和修炼,在控制中达到线条的流动和表现的美感。中国传统对于笔墨的要求带有很强的训练性、控制性,并又提升到人的性灵体现的高度,这是一种“修为”的概念。而当代性即是更强调个体性的表达、情绪,并追求生命的自由。那么,我希望用“游·象”作品来尝试在“修为”的自我控制、自我修养中,达到当代人更高的自由境界。这种控制与自由之间关系探讨,是我一直感兴趣的。
我喜欢矛盾、冲突、紧张感所产生的张力,我在做装置作品时一直在表现这种冲突,情感上的冲突,视觉上的冲突,感受上的冲突等等。
KU:您刚才提到了紧张感,作品中的伤害性,这与您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与当下社会的语境,或与当下时代感受是否也有关系?
W:从哲学角度讲,人来到世上就充满伤害与矛盾,伴随着人的一生。比如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一经使用,它整个“生命”过程就是在不断被损害着,无论对它怎样进行包装或装饰,或细心保护,它已经走向了不断被伤害的不归路。人生也是这样,不断的处于一种有意地自身伤害,与无意之间被伤害的过程。
而在现代社会中,国际上或当下现实总有这样一些问题,在国际上我们深深感受到政治、经济、现实的复杂性,边界问题的冲突,难民问题的产生,经济危机,人的伦理与理想价值的多元与崩溃等等,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中国也是有很多多元的事物,既有辉煌的,令我们非常振奋的东西,也有许多令我们担忧的,需要我们不断面对的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丰富的题材或感受,这些感受如何表达出来,如何转换和传达给观众,让大家来体验和思考某种生命和现实的东西,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KU:您的作品是一种有“痛感”的艺术,这种痛感既有直观的感受,也有进一步思考之后严肃沉重的感觉,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很多是“绿色无害”的,或者说是比较能够迎合中产阶级趣味的,可能看上去也非常亮眼,但背后思考的东西可能在稀释。
W:我的艺术特点是很明显的,这种明显其实也是这一代人的特殊经验所造成的。我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复杂甚至沉重,感受、经验和情感都可能比较“重”,喜欢“重”一点的东西。但是我也很尊重年轻一代艺术家,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对新媒介,对技术问题也很敏感,情感与认知等方面也比较轻松和乐观,他们自身经历本身就可能有比较多的欢乐,所以他们希望非常轻松地面对艺术,面对人生,也想用一种非常亮丽的艺术作为载体来予以表现,这都是很正常的。
从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偏向于艺术应该有某种痛感,或某种触动感,这种触动感可以有很多种,我第一次看到徐冰的《何处惹尘埃》时,一下子被震惊了,觉得太精彩了,艺术品应该有一种令人说不清楚,却又很能触动你的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使观众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体验和感受,使观众思考一些东西。
KU:这次展览所有的平面作品都是以漂浮的形式置于墙面上,与装置作品形成一种很好的呼应,您还为配合展览空间特意创作了一批作品,这次的空间与您的作品之间有怎么特殊的关系?这次展览的布展方式,作品体量都与以往有许多不同,这是否是您艺术道路上的一次突破?
W: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突破吧。这次展览比较有意思是民生美术馆的空间,很多艺术家觉得这个展览空间特别好,但它是旧工厂改造的,有很多特殊性,如何驾驭这个空间需要挑战。这次我也有意面对这样一个空间去做自己新的尝试,针对展览空间与我的空间设计师孙华等进行了很多讨论和实验,巫鸿老师也给了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根据这次展览空间产生了一些新的作品,或者说将原来的作品进行一种新的改造,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此,这次展览有很多新的呈现方式,也有很多新的突破,比如前面提到的《缠2》,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平台上进行的一种新的创造。我对这种空间设计和空间挑战很感兴趣,对自己也是一次超越。
KU:“墨线”带有传统文人气质,是与自然相关的一种表达,而“铁丝网”则是人工的,危险性的,两者在语言形式上有共通之处,但又是极为不同,您为什么会将“墨线”逐渐衍变为“铁丝网”?
W:其实两者是并存的,也有演变转折的过程。《游·象89》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在进行这幅画面创作时发现,看似柔弱的“游?象”线条可以表现出很刚强的,甚至是铁丝网的感觉,它触动了我进行铁丝网系列的新创作。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一方面会沿着铁丝网的思路进行一些新的综合表现,另一方面仍然在“游?象”系列中进行一些探索和延伸,并不是一下子就放弃“游? 象”系列,而是两者并存的创作思路。
KU:中国水墨是一种个人内心的表达,与艺术与否无关。您从小学习传统绘画,也有深厚的传统文人修养,您在最初从事水墨艺术时是否也是将其作为一种个人喜好?
W:中国水墨比较重视个人修为与个人生活及精神的体验,这是非常重点的。我父亲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我从小就被手把手地学习水墨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成长,使我对水墨有较深的体会和兴趣。当然我也画过很多油画作品,觉得还没画好没有拿出来,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用水墨,或用一些材料来表达我对社会的感受,对个人的感受。
KU:您的水墨作品已经摆脱了传统创作方法,而是采用纱布,绷带进行拓印,引入这种充满伤痕感的材料,包括用纱布蘸上红色拓印十字架,水墨对您来说是否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生命的习惯?
W:如果将水墨作为一种材料转化为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并且能够非常和谐一致,自然而然进行创作的话,那是非常好的状态。艺术家应该去发现一种材料,像水墨、铁丝网或玻璃管,它们跟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能够形成一种契合,能够更好的发挥材料本身的特殊意味,而转换成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想这是较好的结果,我也努力去这样找寻和尝试。
KU:您做了很多年的美术馆馆长,也与国际上的当代艺术界有很多交流,相较于一般艺术家,有更多样化的经验和结构,这些经历对于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念有什么不一样的帮助?
W :确实这些经历对我有很多帮助,人的经历必须丰富,美术馆馆长的身份,工作中的经历,与国际之间的交流,从视觉经验到认知经验的转变,所有这些都使得我的生活非常丰富。任何人生活都可能很丰富,如何将这种丰富的生存经历转换成艺术创作,这需要自身的修炼。
我的经历很特殊,我从小在一个比较古典的家庭里成长,这个古典家庭又受到各种时代、政治、人与人关系等原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压抑和破碎感。这种成长过程给我的学习和生命感受带来了很多既波折又丰富的东西。后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包括后来转换的两三次工作都与机械有关,在街道办的生产组,在机械工场等等。我是从工厂最基层走出来的,这使得我对机械和严谨性非常感兴趣,也使得后来我对美术馆的管理比较注重条理和细节,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历。后来在美术馆工作,能够与一些国际美术馆、策展人、艺术家交流,也使我创作的思路和眼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这次展览或者说我的创作,是在努力从日常经验和工作经验里找到一种感觉,这个经验都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是个人的,这种选择没有办法进行比较。最近我看到今年卡塞尔文献展上有一件铁丝网的作品,是一个外国人做的,在货架柜上摆了一捆一捆很整齐的铁丝网,感觉也很不错,有另外的一种寓意。外国人做的作品很直接,中国人做作品,或者我个人做作品可能想有更多的丰富性,更多其他的东西。
KU:本次展览主题为“边界/空间”,边界是一种限制,对边界的突破又是一种自由,您从小的经历,美术馆馆长的身份,艺术家的身份其实都是一种限制,在如此多的限制和对于限制的突破当中,个人如何安身立命,寻找自己的自由?
W:我想,做美术馆也好,做一些创作也好,做人也好,都是在矛盾之中。如果以美术馆的工作为例谈这一问题,美术馆工作中存在着很多边界限制,包括资金限制,人的限制,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要做好一个美术馆,或者做好一个美术馆馆长,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判断,任何事不能太多地受到周围及条件的束缚和影响。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要有能力或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克服某种限制,找到自由。这也许就是“边界”和“空间”的关系。
KU: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一种限制和自由之间不断处理这种状态的交替,安身立命是中国传统文人就是求艺问道的终极目标然后您的艺术语言看似是形式是当代的,其实有很深厚的传统修养,您艺术是否也是您个人得安身立命的方式。
W:“安身立命”这四个字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对传统中“安身立命”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有很多古代文人都有某种志向,有自己的一种作为来实现自身理想。“安身立命”应该转化为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身理想,有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觉得艺术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个人也好,都应该去寻找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拒绝,可以参与,可以对抗,也可以回避,但是应该是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坚守的方式,而不是芸芸众生的方式。